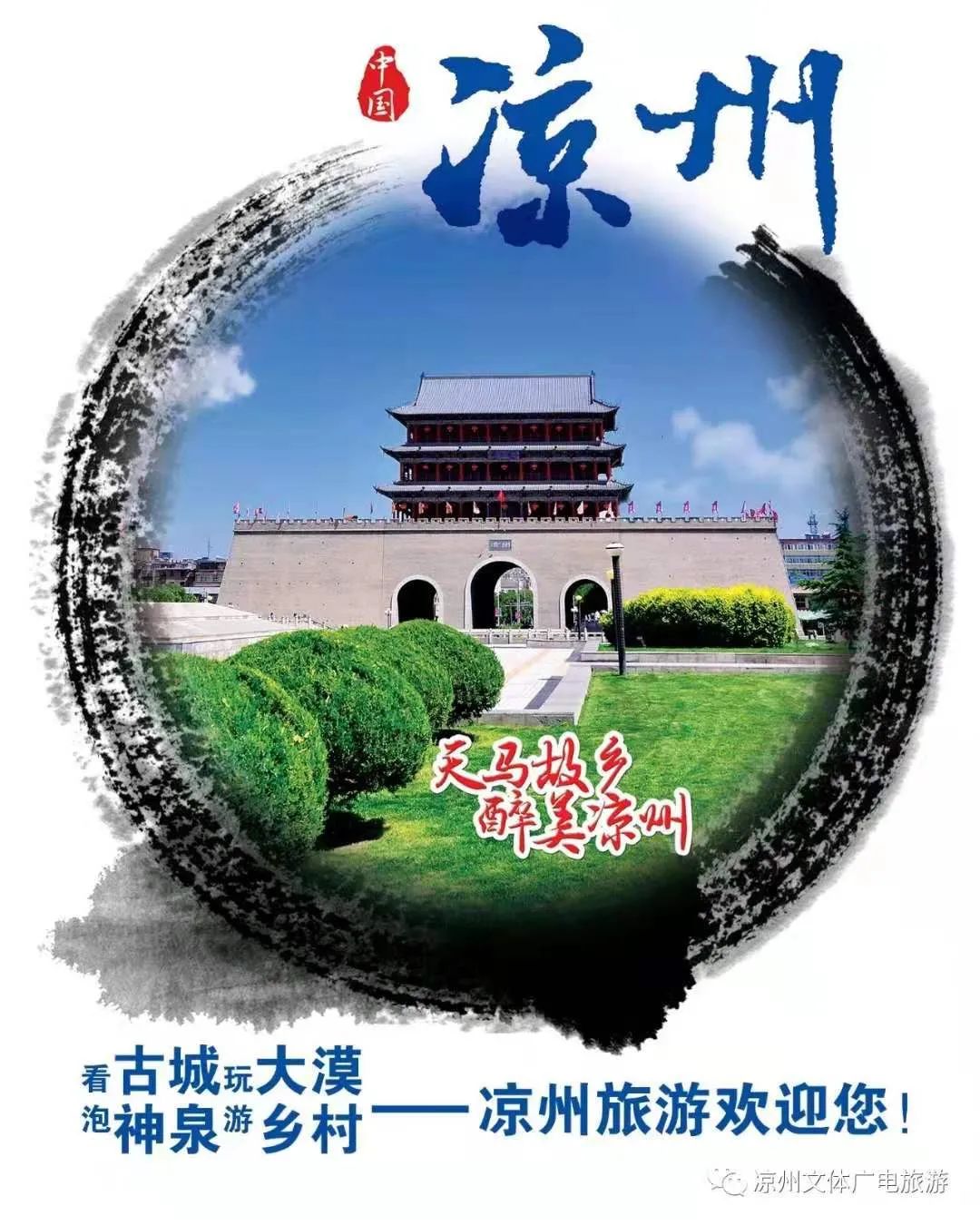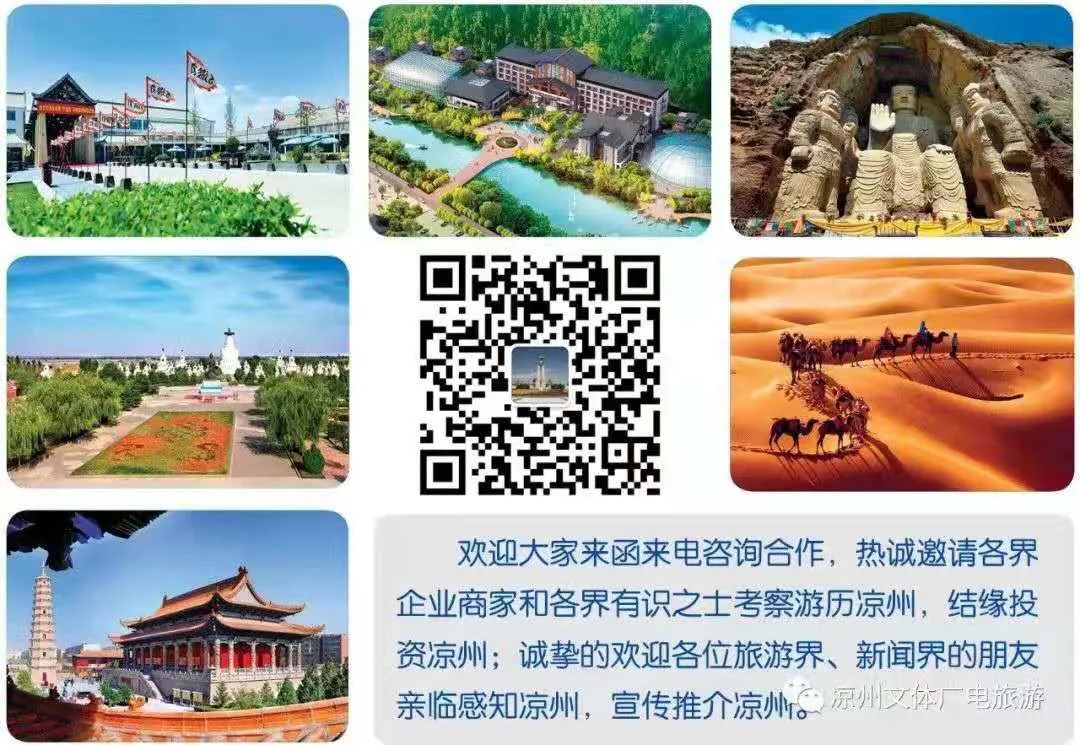挥不去的乡愁,留得住的乡味:武威臊子面

导弹熊,原名肖彧,甘肃凉州人,现在北京工作。为电视评论主笔,专栏作家,电台军事节目主持人。自称不可救药的话痨,不写就会死的码字工。深读历史后喜欢歪解,博览群书后善于跑题。至于这里,玩的是新闻穿越感,打的是时事擦边球。所以用他独特的视角,从另一个方面全面阐释了家乡武威独有的特色小吃,读后让你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家乡味之臊子面
形容一碗面,用词有风险。
若只是用香、鲜之类大陆货,人家会说你就会吃,连个像样的修饰都不会。可如果你说一碗面繁花似锦,人家又会说你太夸张,只会像小学生一样,以堆砌辞藻为炫耀。
可繁花似锦有时候不是修饰,就是写实。
我说的是臊子面。
西北戈壁滩一样浩瀚的大碗里,皓然洁白的面条神龙不见首尾。那种白,是上苍对小麦的恩宠,让它在粗糙外表下有雅致的灵魂。林黛玉说海棠“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清雅固然清雅,暗香固然暗香,但未免阳春白雪,距离人们胃肠里的烟火气过于遥远。假如她精通西北面食之道,能够把一个大海碗香喷喷地端到贾宝玉面前,柔声说相公辛苦了吃碗面吧,并在后者吸溜吞咽雪白面条之际,用一方帕子抹去他额上的汗,轻轻吟诵:“偷来隔壁二两面,借得农家一根葱”,估计薛宝钗一毫克戏都没有。

面条是主食,但并非主角。真正讲究的食客,在吃臊子面这种汤面时,追求的是“汤宽”,就是汤水一定要占绝对优势,要像庄子所谓秋水汪洋,要似关云长水淹七军,若还用《红楼梦》典故,则必须反其道而行之,鄙视“一杯曰品”,崇尚大水漫灌。
如果汤少面多,水浅舟大,则有名实之争,会引发土著质疑:“呔!你这个是臊子面还是干拌面!”实际发音:带!泥自个四骚子面(发成后鼻音)杭四杠帮面!
事关荣誉的臊子汤绝非清汤寡水。
肥瘦相间的鲜肉,细细地切成碎丁,事实上细碎肉丁就代表“臊”这个多音字唯一美好的一面。丰硕水灵的白萝卜,细细地切成碎丁。鲜嫩淳朴的豆腐,细细地切成碎丁。愣头愣脑的土豆,细细地切成碎丁。风干后重新回水的黄花菜,细细地切成碎丁。如果香菇乐意加盟,也不可恃才傲物,须细细地切成碎丁。葱花自然是碎花,香菜末自然是碎末。
总之,一切自我都需要克制、压抑小我,咸与维新,共襄盛举,以便成就集体荣光,酿造一锅醇香。

葱花炝锅,胡麻油里渗入葱香,实现西域文化和中原文化的一勺烩。肉丁煸炒到变色,加入三粉:花椒粉、胡椒粉、姜粉,在一种万物都要无障碍进入肠胃的烹调中,花椒粒是不可想象的;舍生姜而用姜粉,也出于同样的考量。有些人家刻意把肉丁炒到略焦,追求那种烧烤口感。酱油不言而喻,或可起用一两粒八角,那样会制造出一种独特的鲜味。其余食材,依据质地软硬,先萝卜,后豆腐,接着香菇,最后土豆。大火开锅,小火慢炖,所有这些食材,都会在高温煎熬、生死沉浮中,失去边缘棱角,牺牲外在品相,接受汤汁洗脑,保留核心本真。土豆介于将化未化,萝卜舍脆取糯,豆腐满身细碎裂纹,最后时节,撒入香菜末,恍如翡翠群星为百宝箱点睛。
今人用味精或,精,前辈不用,一则是没有,二则成功的厨师会用食材的相生相克,自然倾轧出原始本真的鲜味。今天很多主妇自发探索,会用菌类、番茄甚至特效酱油来增鲜,效果也不错。
我得承认,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武威人描述味道,是没有“鲜”这个概念的。这个字当然有,只是发音为后鼻音,我们提到它时,意思是水果蔬菜离开母体不久,还没有来得及发生化学反应。那么怎样表达水族的味觉呢?很简单:无论水陆,好吃的东西一概“香”之。

烹制完成后的武威臊子面卤汤和陕西岐山相比,根本区别在醋。后者在加工中就要放醋,所以无论食客是否嗜酸,都必须接受既定事实。 武威臊子面也不排斥醋,但绝不在加工中引用。优质熏醋在醋壶里,好之者自取。我请外乡朋友吃臊子面,或者自己做了给慕名者品尝,总是会按住醋壶:“你先尝原味嘛!”对于那种不青红皂白上来就醋壶灌顶的做法,我会真诚地恼怒起来。
大约陕西靠近中原,农耕区的粮食不介意醋,事实上粮食就是醋的原料;武威有浓郁的牧业传统,肉食和醋不大相投。至少在我看来,大凉州饮食谱系中,对于醋的介入,有大致清晰的楚河,简言之:凉粉凉面凉皮子之类冷食无醋不欢,而几乎所有品牌热食,原初面目中罕见酸味,肉食尤其如此。
臊子面,在漫长的过去,一直是武威的一种集体主义食物,不仅是因为食材富集,更是因为在婚丧嫁娶这样很多人连续进食的场合,它有一劳永逸之妙:只要熬制出足够量的臊子汤,现来人现下面,无需更复杂的工艺。我见过的宏大进食场面包括:显然刚刚结束军训的中学生、工地厨房外的大群建筑工人、复原回乡的军人、一个导游招揽到面馆的饥肠辘辘的游客。当足够多的人捧着臊子面时,那种虹吸动作制造出的声音,堪称山呼海啸。

小时候的武威城,官办饺子馆一,只有一种馅儿;官办包子馆一,只有一种馅儿;官办臊子面馆一,它恰好在我上学的路上。冬天天亮得晚,我进去的时候,还需要等一会儿。我手里攥着每天颜色变化的小小纸票,看着那个巨大的铁锅里,花花绿绿的食材,恍如寻仙,在雾霭升腾中醉生梦死。有一天我偶然发现大师傅的秘籍之一,那就是他从案子底下一个铁桶里舀出一勺猪油放进锅里,猪油恍如一小队官兵,迅速被造反者的汪洋大海吞没,我正在惊诧,听到大师傅威严的声音:你的票呢?(实际发音:匿抵漂囔?)
我多年后自己做臊子面,用更高级的方式传承了那一勺猪油:骨汤。但正如一切复制家乡饭的企图都在他乡流产一样,在北京做出来的臊子面,品相完整而味道走样。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是因为一方水土成就一方朵颐。武威寒季漫长,历史上缺乏多样化的时蔬,过了夏季,只能靠大路菜维持餐桌,臊子面就是大路菜的集结号,几乎集中了那时候的地产精华,是基于匮乏的丰盈,来自短缺的奢侈。
前不久有好事者在网上排列所谓全国十大面,结果因为明显的孤陋寡闻而引发仇恨。岐山臊子面上榜了,武威臊子面没有。
大凉州那一片的人,古风犹存,不事张扬,在这个忽悠时代,这是缺点。
未来在桃贝勒身上,我希望他努力仕途,做到不知第多少代中央领导核心时,可以小小动用特权,将武威臊子面列入国宴。
那时我存亡未知,或许见不到家乡美食的这一天,不过可以效法古人,以诗为遗嘱: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凉州不飞腾。国宴捧起臊面时,家祭无忘告乃翁。
至嘱,切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