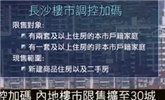八步沙的变化很大 八步沙的故事很多
2020年03月30日 09:36
来源:凤凰网甘肃综合
作者:张尚梅
“又到沙漠里花开的季节。一丛丛、一簇簇、一团团,红的、白的、粉的……”年轻治沙人陈树君取远景、近景,不停地变换着手里的镜头,这些花,开了不容易。

先进群体
大风起兮
对于婚礼,每个人心中都在编织一个梦幻场景。
1959年农历腊月二十日,对于嫁入古浪县土门镇石河湾的新娘胡玉兰来说,这个日子是喜庆而灿烂的。穿嫁衣、上驴车、欢天喜地拜天地、上烩菜,全村老少爷们就等着放开肚子开吃……忽然一阵黄风刮来,天地间一下子变得昏暗,参加婚宴的人群四散开来。
石河湾出门就见八步沙,这场“不识时务”的风就起自八步沙。
八步沙,在地图上找不到它的位置,但它是那条巨大沙龙的龙头——腾格里大漠的南端前沿,也是被世界称为生态工程之最的“三北防护林”工程的前沿阵地。
由于自然的、人为的因素,八步沙的沙丘逐步变大,总面积达4万多亩。吞家园食农田,打死禾苗,干旱、干热风加剧,沙丘以每年7.5米的速度向南移动,已经到了不是人进就是沙进的边缘。
1981年,那是一个难忘的春天。镇村领导碰头会上,漪泉村56岁的老支书石满第一个站出来:“多少年了,都是沙赶着人跑。现在我们要顶着沙进,治沙,我算一个。”六位老汉贺发林、石满、张润元、程海、罗元至、郭朝明郑重地在治沙合同书上按下了鲜红的指印,奏响了同一个音符——治沙,开始了艰难的治沙之路。

沙漠护林
进军沙漠
“正月里来是新春呐,青草芽儿往上升,天凭着个日月啊,人就凭着个心呐……”
1980年冬至,吃过早饭,6个年龄差不多的中年汉子相约来到古浪县八步沙了解地形地貌。一路上,他们唱着小调给自己打气,这漫漫黄沙怎么治,谁心里也没有底。
1981年春,古浪县首家联户经营的林场——八步沙集体林场正式成立。
在沙地上挖个坑,上面用棍棒支起来,再盖上草和沙子就是房子了。他们管这种房子叫“地窝子”。白天在沙漠里干活,累了,抽几口旱烟解乏;冷了,生一堆柴火暖身。做饭的时候,风沙揉进面里、刮到碗里,吃进嘴里,牙被硌得直响。
在风沙肆虐的沙漠里播绿,谈何容易?他们用双手挖出埋在沙里的树身,手捧黄沙埋住被风掏出的树根,硬是让一棵棵树苗在八步沙这片荒漠上扎下深根、发出绿芽。6个家庭40多人全部上阵,最小的10多岁。他们还动员各自的亲朋好友50多个劳力,在浩瀚的大漠里播下一株株绿色的种子……

合力压沙
决战黄沙
沙漠,有一种狠,凶猛无比,常常深夜袭击行人、骆驼和马匹。罗元奎就深深感受过沙漠的狠,一种惊心动魄、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狠。
1993年4月的某一天,罗元奎老汉在睡梦中忽然听到轰隆一声闷响,就失去了知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一股浓重的中药味满屋子弥漫,才知道“地窝子”倒塌了……
“终于醒了,吓人哩。”石满凑到跟前,给他掖掖被子,抹了一把泪。“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张润元安慰着罗老汉,“受惊了,好好缓几天吧,看你这身子骨。”他欲言又止。罗老汉问:“窝铺塌了,又得重新盖?”说完,他涌出大滴大滴的眼泪。心沉沉的,如同压着一块石头,不仅窝铺塌了,他还担心昨天种的树苗是不是又被连根拔了。罗老汉暂时不能值守了,石满重新给大伙排了班。
育林人的意志,在反复的栽种里牢牢生根。1982年,他们又种了4000亩的树,为了有足够的草,以草保树,他们推着小车,走村串户的收干麦草,甚至卖掉了准备做种子的土豆。
沙漠迷路
春天风大,沙漠上有的是旋风,一股一股的,把黄沙卷起好高,像平地冒起的大烟,打着转,人也时常被卷着飞跑。
夏天,处处热浪滚滚,沙漠里热得像个火炉,仿佛燃烧着熊熊火焰,最高温度达42℃。身上的汗随时被蒸发掉,水壶里的一点水,喝一口润润嗓子不敢咽下去。
冬天,近处漫漫黄沙,远处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天是蓝的,地是黄的,除了蓝黄两色,再也看不到其他的色彩,护林员在沙漠里一步一步跋涉,广袤的大漠,死寂的沙海,那种安静让人害怕。最可怕的是下了雪,沙漠里地形到处都一样,一下子叫人辨不清方向。有一次,贺发林晚上巡沙漠时遇上了下雪迷了方向,早上一看才知道自己围着一个沙丘走了一夜。
尽管风餐露宿,但他们还是坚持了下来。1984 年春天到了,在六位老汉的心上,这是一个真正的春天。前一年栽的树,成活率为78%,看着一棵棵幼苗发芽抽叶,六个铁骨铮铮的汉子心里比喝了蜜还甜,面对满眼的嫩绿,他们竟像小孩子一样,高兴得泪光闪闪。
种树老人
农村有句古话:“活着享福不如死后一副好棺材。”在一些老人眼里,死后有一副好棺材才是对自己一生最好的交代。
1990年的深冬,贺发林的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
“贺爷,你百年之后,就用自己种的沙柳做口‘老房’吧!”亲朋好友提议。“舍不得啊,舍不得……”贺爷哽咽着再没说出一句话。临了,他也没舍得砍下一棵沙柳。
那年,贺老汉准备打一场有准备的仗。催着老伴装满一布袋子的馒头、土豆、胡萝卜,在驴车后面装上麦草、水桶、铁锹、油灯、一把生锈的茶壶和几袋旱烟就出发了。风呼呼地刮,漫天都是黄沙,嘴巴里、鼻孔里、衣服鞋子里全是沙子粗糙的触感。夜间,黄风还是没有消停,狂怒地掀着沙子,一股脑儿地向房顶上抛撒。听见窝铺顶吱吱呀呀像要坍塌,贺老汉赶快掀开被子,顾不上披上外套就跑了出去。还没走出十步,经不住沙丘的重压,房顶轰隆一声坍塌了。
几经艰辛,六老汉终于在沙窝窝里种上了近1万亩的树苗。第二年春天,成活率达到70%。
贺中强曾悄悄问父亲:“面对没有尽头的沙漠,努力做着没有尽头的事,值吗?”贺发林说:“树活了,我的心就活了。”树是活了,但贺发林昏倒在树旁。1991年,贺发林老人垂下了枯瘦的双手——“回”了。
“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来年春天,老人坟旁的树冒出新芽,矮小但粗壮。路过的村民看了都说,那就是种树老人。

网格治沙
守望家园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守望平静的家园。”一位诗人曾写过这样的诗句。
石满不是诗人,但他有着和诗人一样的心愿:“把我埋到能看见八步沙的地方。”
沙漠的容颜是那么苍老,每一道褶皱里都刻着旱魃和狂风侵扰的创伤。看着一望无际的沙漠,20岁的小伙子石银山眼睛里充满了迷茫:“爹,就凭我们这些人,压住这漫漫黄沙,不是愚公移山吗?”石老汉不吭声,拿起铁锨一脚踩下去。第二天傍晚,石满躺在了自家大炕上,挖沙的时候,他的脚崴了。
伤筋动骨一百天,石满在炕上躺了十天就坐不住了,第十一天一大早,他就拄着拐杖巡林去了。八步沙附近村里的孩子杨先和小伙伴一同骑着骆驼去沙漠放牧,在攀上沙枣树、依着树枝细细品尝红红的沙枣时,被石老汉一声吆喝吓得滚了下来。杨先纳闷:“沙枣树在沙窝里,骆驼在沙湾里,他怎么看得见?”可是,那个身材矮小、脸庞黝黑的干巴老头确实从沙枣树枝条中探出头来,目光犀利。
1990年秋季造林时节的一天,石老汉骑着毛驴去巡林。中午1点多的时候,毛驴回来了,可他还没来。儿子找到他的时候,人昏倒在沙漠里。1992年,62岁的石老汉在挖树坑的时候再次昏倒。生命弥留之际,他留给后人的一句话是:“把我葬在八步沙,我要一直守护着这片林子!”
如今,在八步沙,沙止步、绿成荫。石老汉的坟就在这里,尽管离家很远,但离八步沙很近、很近、很近……

生机盎然
绿色梦想
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郭朝明没有停止治沙的脚步。云卷云舒时,他就势躺在沙砾上,抬头仰望天空。一粒粒细软的沙活动着,和着徐徐的风吹拂在脸上,酥酥麻麻,一身的疲倦瞬间褪去……
郭老汉梦见,自己变成一颗流星,划过长空,落在了八步沙。感觉自己不久于人世,郭老汉给儿女们交代了三件事:早点准备来年的草;去国营农场再要点树苗;从长计议,解决大家的生计问题。三件事,没有一件涉及自己,涉及家人。
新墩岭是明长城在古浪段土门镇东隅与八步沙一河之隔的一个烽火台,它的北侧是台子村的一块旱地,有300多亩。到上世纪70年代初,新墩岭的春天却被黄风笼罩,一年下来,这300多亩地没多少收成。找铁锹、买水桶、收麦草、购树苗……郭朝明毫不犹豫辞去生产队长职务,承包了一块不能耕种的土地,开始了他的“绿色梦”。
一天,植树的时候,郭朝明的旱烟袋丢了,急匆匆去寻找。走出地窝子不远,不经意转过一个弯,在一座沙岭背后,几棵葱葱茏茏的沙柳在风中昂扬,柠条和梭梭开着小黄花,一朵挨一朵,几只黑色的蝴蝶在上面忘情地追逐,翩翩起舞……
2005年,已有8万多株沙生苗木在沙漠里“挺立”,有风时树影婆娑,没风时飘逸秀美。2005年,60岁的郭老汉植完最后一棵树,再也没有醒来。
善意谎言
郭万刚说,自己曾对爱人陈迎存说过三次谎,都是为了治沙。
郭万刚对陈迎存第一次说谎是1983年,他准备辞去“铁饭碗”,正式进八步沙林场。
一天,快到晌午吃饭的时候,村民张尕娃慌慌张张跑进窝铺去报信,郭万刚女儿小红病了。在乡卫生所,输了液体,小红的脸色渐渐恢复正常。陈迎存这才回过神来,埋怨起郭万刚:“你说,还辞不辞职了?辞了职,我们喝西北风去?”“不辞了……”郭万刚心里盘算着,辞职报告已经递交上去了,缓些日子再解释吧。
“再不说谎”这句承诺维持了15年,郭万刚不得已说了第二次谎。
农历大年三十,郭万刚雇了一辆大卡车去金川公司拉打井的设备,回到家已是第二天凌晨4点,天露出了鱼肚白。在后车厢坐了一夜的郭万刚捂着肿胀发热的腮帮子一次吃下了3副剂量的感冒药。怕要账的人在家里等,更不想让媳妇跟着担心,郭万刚长叹一口气,不得不再次说谎:“小李子,去我家里,给我媳妇说,货没拉上,我还没从金昌回来。”浑浑噩噩睡了5个小时后,郭万刚被程生学摇醒:“贷款到位了。”他喜极而泣地说:“得回家看看。”快到门口的时候,看见一辆三轮车上坐着五六个女人正朝着自家大门的方向开去,郭万刚心里明白,这是来要账的。
郭万刚家院子的红色大门敞开着。墙根是一蓬一蓬的水蓬,叶梢被太阳晒得枯黄,窗台上挂着一串串红辣椒,西厢房门边上的簸箕里晾晒着一个个像小伞一样的“栀子面”,9岁的女儿郭金秀踮着脚尖在贴对联,6岁的小儿子郭义帮姐姐端着浆糊,大黄狗窝在门台上摇着尾巴汪汪地叫着……陈迎存端着一锅刚做好的烩菜一脚踩在门槛上,问:“车上啥人?”郭万刚悄悄擦了擦眼角,心里五味杂陈:“拜年的,怕吵着生病的老父亲,打过招呼走了……”
三次善意的谎言、三次艰难的选择。想起对父辈们的承诺,郭万刚再也没回头,留在了八步沙。那一年,他31岁……
青春绽放
生在沙漠边,长在沙漠边,郭玺的童年生活,几乎与黄沙相伴。
冬天的早晨,寒风“呼呼”地刮着,两岁的郭玺蜷缩在被窝里喊一声爷爷,听不见回应。奶奶说,爷爷天没亮就进沙漠了。那一年,爷爷把郭玺背进了沙漠。爷爷教他认识红柳、花棒、柠条……开始了他认识沙漠的第一课。
背草、压方格、植树……转眼十几年过去了,郭玺在沙漠里摸爬滚打,长成了一个健壮的小伙子。如今,郭玺负责操作林场里各种机械,还管理着八步沙“溜达鸡”鸡场。尽管初中没毕业,拖拉机、装载机、抱草机、打坑机、洒水车,各种机械样样精通。
2018年,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的先进事迹先后在《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甘肃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图片展览展出、中宣部授予古浪县八步沙林场“六老汉”三代人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称号……一件件喜事接踵而来。郭玺心想:啥时候把沙漠种成绿洲、种出花海,那才叫骄傲呢!

喜上眉梢
点沙成金
“又到沙漠里花开的季节。一丛丛、一簇簇、一团团,红的、白的、粉的……”年轻治沙人陈树君取远景、近景,不停地变换着手里的镜头,这些花,开了不容易。
陈树君是地道的古浪人。打小就听周围人说八步沙“六老汉”治沙的故事,心中对他们充满了敬佩。2016年夏天,他到了八步沙林场工作,成了这里的第一位大学生。
树木成活率不高,沙漠里没路……小陈看在眼里、急在心上: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让治沙人治沙又致富?2016年夏天,林区内发生了虫害,大面积的花棒死了。陈树君通过虫情监测仪,迅速扑灭了虫害,充分显示了科学治沙的威力。同时,他和场里商量,开始探索一条治沙与致富双赢的路子。邀请省内外专业技术人员培训肉苁蓉种植技术;发展肉苁蓉产业;带领大伙发展林下经济,注册“八步沙溜达鸡”商标,线上线下销售;联系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治沙造林,用“互联网+治沙”的模式,打破了时空和地域的限制。
八步沙人说,大学生来了,场里变化不小。陈树君回答:“‘六老汉’能用白发换绿洲,我们为什么不能用科学手段‘点沙成金’?”
……
[责任编辑:杨文远]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