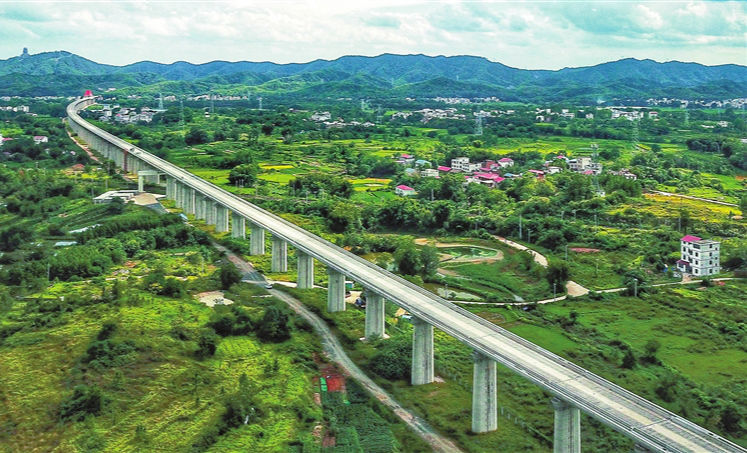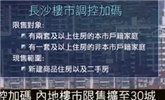追寻敦煌旱峡玉矿“玉石之路”
2020年05月21日 06:54
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作者:陈国科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揭晓,我省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入选“十大考古”。评审专家在点评中谈到,虽然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但是对于玉矿的来源,我们一直不太了解。我们欠缺真正能把玉矿和出土的玉联系起来的证据和途径,而旱峡玉矿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我们追溯玉文化提供了直接证据。
原标题:【走近考古】追寻“玉石之路”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局部)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半地穴式房屋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出土的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陶片。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出土的戈壁料

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半地穴式房屋

寒窑子草场玉矿全景(西北-东南)(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近日揭晓,我省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入选“十大考古”。评审专家在点评中谈到,虽然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玉文化,但是对于玉矿的来源,我们一直不太了解。我们欠缺真正能把玉矿和出土的玉联系起来的证据和途径,而旱峡玉矿遗址的发掘和研究,为我们追溯玉文化提供了直接证据。
一时间,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了敦煌旱峡玉矿遗址。那么,敦煌旱峡玉矿遗址发掘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本期特邀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旱峡玉矿遗址项目负责人陈国科带大家一探究竟。
河西走廊地区早期的玉矿遗址
玉文化是东方文明、特别是华夏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玉料来源研究是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上世纪以来,随着我国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及大量透闪石玉器的发现和出土,学者们开始探讨内地透闪石玉料的来源问题,并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西北地区,提出了“玉石之路”“昆山玉路”“和田玉路”之说。
但和田玉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进入内地,学界尚无定论。玉料的来源及贸易研究,对揭示早期社会先民的活动范围、社会组织形态及相互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稀有资源的利用与社会复杂化进程等都有重要价值,但学术界对此研究仍很薄弱。
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多家单位持续开展了“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先后发现了马鬃山径保尔草场、寒窑子草场和旱峡玉矿遗址。
2011年以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开展肃北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发掘的同时,在马鬃山及其周边地区开展了调查工作,于2014年新发现了马鬃山寒窑子草场玉矿,2015年新发现了敦煌旱峡玉矿。
从考古学意义上看,这三个玉矿遗址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旱峡玉矿遗址是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早期玉矿遗址调查、发掘的重要发现,也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矿遗址。
旱峡玉矿与马鬃山径保尔草场玉矿、寒窑子玉矿遗址的发现,证实了自公元前两千纪初至公元前后河西走廊西部地区的玉料开采活动,对了解我国西部地区玉料来源、开采玉矿的族群、玉矿采集群体的聚落形态、早晚不同时期玉矿开采者的生产组织和管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的发掘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足以显现出玉矿遗址发掘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在发掘中产生的种种认识与问题,也为后期考古发掘与调查研究埋下了伏笔。
玉矿遗址的发掘
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位于马鬃山镇西北约20公里的河盐湖径保尔草场,面积约6平方千米,是目前国内所见规模最大玉矿遗址。地表可见矿坑、房屋、防御性建筑、石料堆积等遗迹383处,整体沿矿脉走向呈西北至东南向分布。2011年-2017年发掘面积5400余平方米,清理房址124座、灰坑112处、石料堆积43处。可见中原汉文化和骟马文化两类遗存,年代为战国至汉代,碳14测年为公元前390年至公元前60年。
寒窑子草场玉矿遗址,位于马鬃山镇东北寒窑子草场,面积0.5平方千米。2014年调查确定矿坑、石料堆积、防御型建筑等10余处。各类遗存依东西走向矿脉分布于山体两侧。该遗址文化面貌与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基本一致。
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位于敦煌市东三危山后山的东南部,西北距敦煌市约68公里。遗址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共发现地面遗迹145处,其中矿坑114处、矿沟8条、岗哨12处、房址8座、选料区3处。2015年调查确认玉矿矿脉三条,确定矿坑、岗哨、房址等各类地表遗存188处。2019年发掘面积300平方米,清理房址、矿坑、岗哨等12处,其中地面石砌房址1座、半地穴式房址5座。遗址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为西城驿文化和齐家文化遗存,碳14测年为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700年;晚期为骟马文化早期遗存,碳14测年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400年。
三处玉矿遗址均为由防御区、采矿区、选料区等组成的采玉聚落址。矿坑多为顺山体开采形成的近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的浅坑,口大底小,矿坑周边堆积大量的石料。防御性岗哨位于山顶,房址、选料区多位于山体两侧近底部的缓坡上。呈现出山体顶部岗哨、中部矿坑、底部房址和选料区的分布特征。
旱峡玉矿房屋分布较为疏散,以单间半地穴式为主。而径保尔草场玉矿遗址房屋分布较为集中,整体呈圆形,可划分为多组,有半地穴式和地面式两大类,以半地穴式为主。三处遗址所见半地穴式房屋平面多呈方形,有单间和套间两种,结构基本相似,主要由柱洞、门道、储藏坑(台)、土台(炕)、操作坑(台)、灶台、地面等几部分组成,部分操作台上有砺石。多数房屋存在改变形制、多次使用的情况。
三处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有陶器、石器、铜器、铁器、玉料、石料、皮革、植物遗存、动物遗存等。陶器主要为生活用器,石器多为采矿、选料的工具石锤、砺石,也有少量的生活用具如石刀、纺轮。相比旱峡,径保尔出土有较多的铜、铁器,铜器主要有武器、工具和装饰品等,武器以箭镞为主。铁器有武器镞、矛、剑、刀及工具斧等。玉料多为山料,有少量戈壁料,颜色有白、青、青白、黄、糖色、青花等,其中黄白玉和青玉比较常见,颜色饱和度偏低的黄白玉最为特征。玉料主要矿物为透闪石,玉化好的样品透闪石含量95%以上,品质好者透闪石含量更达99%以上。玉料具有柱状变晶结构-纤维交织结构,其中柱状变晶结构和纤维交织结构混杂出现者常见,致密细腻玉料的透闪石颗粒在5-20微米左右,部分粗粒的达20-100微米,玉料的折射率1.61-1.62,平均相对密度在2.95左右。
玉矿遗址的发现不仅为北山及祁连造山带软玉成矿研究及找矿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也为寻找该地区潜在的古玉矿遗址提供了借鉴。
河西走廊玉矿遗址发掘意义何在
河西走廊玉矿遗址是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一批集采矿、选料、防御等于一体的采矿聚落址,直观呈现了自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时期至骟马文化晚期、西汉早期近2000年间甘肃西部地区透闪石玉料开采、利用的景象。敦煌旱峡玉矿遗址中,早期可见西城驿文化、齐家文化遗存,很可能是两支人群共同开采;晚期只见骟马文化陶片,较径保尔玉矿遗址所见骟马陶器年代偏早,此时期应为骟马文化人群独自开采玉矿。径保尔玉矿遗址为战国至西汉时期遗存,从两套陶器共存的情况来看,当时骟马文化和汉文化两支人群在这一矿区共同从事采矿活动。寒窑子玉矿开采利用的最早年代和人群与径保尔草场玉矿相同,发现的一处斜井形制不同于其他矿坑,周边采集到青花瓷片,推测此井为明清时期开采形成。玉矿遗址群的发现对研究玉矿开采及相关采矿技术、选料技术、行业组织、社会管理等各个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几处玉矿均发现于河西走廊西部,分处北山山系和祁连山山系,这里是先秦典籍中相关地理探讨的重点区域。如早期“三危山”及“昆仑”之地望,古今学者众说纷纭,而持“三危”即今敦煌三危山、“昆仑”即今祁连山者众。当然也有学者直言,将敦煌的三危山附会为《舜典》《禹贡》所说的“三危山”以及由此引申为敦煌古史开端的种种言论,悉皆无稽之谈。
《尚书·禹贡》载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球”“璆”为一字。《管子》载“昆仑之虚不朝,请以璆琳琅玕为币乎”,《尔雅·释地》亦有“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之记录,《史记·夏本纪第二》中更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三危既度,三苗大序……贡璆琳、琅玕”的记述。《尔雅》、郑玄注《尚书》等古籍对璆琳皆释为美玉或美石。
著名地质学家章鸿钊认为璆琳考之有二,一即青金石,一即青玉或碧玉,而其名疑自青金石出。学者杨伯达认为球琳即璆琳琅玕,系禹贡雍州之贡品,亦即西北之美玉,以白、青白、青色为重。主要产地为昆仑山、金山以及格尔木、祁连山和玉石山等,以“球琳”作为西北之美玉的总称谓。若从此说,则今敦煌旱峡玉矿所见透闪石玉可能为当时“球琳”内容之一种,这便与《史记·夏本纪第二》中“三危既度,三苗大序……贡璆琳、琅玕”的记录形成了高度的契合。我们虽不能据此就能断定先秦“三危”即为今敦煌三危山,但河西玉矿的发现,将为我们认识“三危”及“昆仑”之地望提供了新思路。
而几处玉矿所呈现出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所在区域海拔较低,成矿层较浅,矿脉多有露头。与新疆和田玉山料所处海拔较高古人很难开采利用的情况不同,这里便于古人找矿和在矿脉露头处露天开采,这是甘肃西部地区玉矿资源很早就被开采利用的一个主要原因。河西走廊地区是我国早期铜冶金的重要发展区域,这里的先民们很早就掌握了找矿、采矿技术。大量铜矿、玉矿遗址的发现,表明河西走廊地区曾经生活着一群在找矿、采矿等方面有着丰富经验的人群。从铜矿的寻找开采,到玉矿的寻找开采,相关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借鉴与传承,可能是甘肃西部地区玉矿资源很早就被开采利用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这些大量优质透闪石玉料的存在,为我们重新认识内地早期文化中玉器玉料的来源、西玉东输的路线及其形成时间等提供了新的证据。目前所发现的古代玉矿开采遗址可能仅仅是昆仑、天山、阿尔金构造带、贺兰山构造带附近透闪石大型成矿区部分的地表出露矿点,其下可能有大量潜伏的透闪石玉矿资源,河西玉矿遗址的发现,对寻找透闪玉石矿资源也具有启示意义。
根据科学检测分析显示,山西下靳遗址的玉器玉料来自于敦煌旱峡玉矿,径保尔草场玉矿是徐州狮子山玉器玉料矿源之一。一系列证据表明,甘肃地区的透闪石玉料很早就进入到甘肃以东及周边区域,在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作用。
相关新闻:
甘肃日报:【相关链接】考古人的真实工作状态

发掘现场

现场探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魏美丽
在大众的印象里,考古工作很神秘,工作状态也是一帮老学究拿着放大镜翻阅文献的样子。我经常会被质疑:“你是搞考古的吗?我以为考古的人都是老学究呢!”
那么,真正的考古工作是什么状态呢?
每一个考古项目的开展都有着相似的经历,那就如同苦行僧的修行一样,是艰苦和执着,但是研究的内容却是千差万别。就拿甘肃境内的河西走廊早期玉矿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来举例。
考古工作是一个严谨的科学,它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深入田野工作前期的准备工作,这要求考古队员们阅读大量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材料,进行反复的研究和推敲,确定研究方向和目的,框定大概的调查发掘范围;其次是申请考古调查发掘执照;再次是采办调查发掘需要的各种工具和仪器;最后,大家才能按照计划,开启考古项目的调查发掘之路。
初期调查时,难度会大一些,会遇到许多无法预知的困难。马鬃山深处荒山秃岭、影影绰绰,茫茫戈壁,无边无际。扑面而来的荒凉和孤寂是这片土地给人的第一感觉,放眼望去,只有光秃秃的群山和戈壁,极目远眺,那戈壁的尽头就是天际。有时候一天都碰不到一个人,更别说有村庄可以歇歇脚了。
陈国科和队员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着调查工作。每天在出发前都要准备好充足的口粮和饮水,干面大饼、泡面、旅行壶、保温壶、矿泉水,这些物资是必须要带够两倍的用量。即使是炎热的夏季也一定要带上棉衣,这里昼夜温差大。如果一天的行程顺利,至夜能返回驻地;如果不幸遇上沙尘暴或突发状况,这些食物最少能保证大家不饿肚子。
车辆只能在较为平坦的戈壁滩上行驶,大部分位于深处的地点只能靠队员们徒步。队员们带足了水和干粮还有罗盘资料等设备,经常跌跌撞撞在戈壁里求生一般展开摸排调查,这要花费很长的时间,需要的是坚强的毅力和耐心。有时会碰见戈壁狼狗,惊出一身冷汗;有时踩空摔倒划伤,抓一把黄土就能止血;有时碰见沙尘暴,浑身上下都是泥沙,耳朵里的沙子几天都掏不干净;有时也能碰见姿态优美的黄羊和游走的壁虎……这些如同“探险家”一般的经历,令队员们一直记忆犹新。
队员们遇到地面有陶片、石器等人类活动过的地点,一定要详细地记录和标记。最后由这些标记点连成线,确定哪一个地点人类活动最频繁,并作为重点区域进行小面积发掘。
白天上工地发掘,晚上整理记录图纸,查漏补缺,修补陶片,分析讨论发掘现象,总结经验教训。队员们租住在离工地最近的农户家里,大家要在工地上一起生活、工作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现代科技手段不仅为考古调查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更为考古工作带来了便利。在没有无人机航拍时,队员们为了获取一张遗址全貌照片,就必须爬上紧邻的山头或者找了梯子登高,照片效果还是不够全面清晰,这为后期资料的储存和调查分析研究带来了诸多不便。现如今,有了无人机新兴技术,不但有了全貌的照片,还可以生成三维动态图,放大后就连细节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些看上去很“土”的考古人,通过不断地学习新兴技术,用高科技手段为现代考古插上了飞翔的“翅膀”。
在发掘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难题。大家要从地层中细微的土质土色的变化来分辨出是不同时期形成的活动层,还是大水冲刷的淤土层,或者是其他堆积层。干燥的土层看上去都是一样的颜色,这就不得不借助喷壶,一遍遍地喷洒,一遍遍地分辨。遗迹现象相互叠压打破、被破坏的现象是每个遗址都会出现的,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能从地层上客观地说明遗迹的早晚关系。所以,弄清楚这些有关系的遗迹到底是房址还是灰坑?谁打破谁?谁早谁晚?内含的陶片等又是哪个位置的?这些都需要反复观察、推敲、探讨。有时候这种解决不了的难题就像拦路虎一样,使得发掘工作无法继续下去。在发掘现场,有时会看到有人手持手铲,眉头紧锁,一会蹲下仔细端详,一会围绕着遗迹来回转圈,这说明他一定是遇到了难题。
每一处古遗迹都是唯一性的,它不可再生;每一次的考古发掘活动也是唯一性的,所以发掘过程中的每一步记录和考古队员的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这要求队员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都必须详细做好考古发掘记录,为日后研究打好基础。
考古发掘现场,除了铁锹开挖、手铲刮面、记录详情、测绘平剖面图、拍照遗迹、分拣各种出土标本,还有一件工作不可或缺,那就是浮选地层土样。
一堆堆一捧捧的黄土,看上去与平常无异。当我们对不同地层的土壤进行细致地筛选后,又会有怎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地层土壤中包含了珍贵的线索,当时生存环境的信息,有什么植物生长,吃的什么,有什么样的动物共生等,筛选完细腻的土壤后,颗粒较大的孢粉、种子、细小的动物骨骼碎渣等都被筛了出来。经过淘洗后,还有碳化植物残留物……这些标本通过后期的科技检测,就为判断当时的生态环境提供了科学依据。
考古工地结束后,更加艰巨而精细的修复、研究工作转入了室内,大量破碎的陶片清洗、编号、拼接、复原、绘图、扫描,各种标本的检测、分析、统计,每一份记录的研究、分析、筛查,整个遗址相关文献、考古资料的梳理、分析、比较……最终成文,公布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后,完整及复原的文物才能交到博物馆对外展示。
在文物背后的发掘工作中,考古人员会面临很多危险和困难,经历许多的艰辛。他们常年与田野做伴,凭借着一腔热爱和情怀,让事实说话,佐证历史。
[责任编辑:张蓝翔]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