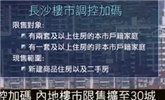追忆那刻骨的敲打与棒喝:樊锦诗和宿白的师生情谊
2018年10月24日 10:43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作者:顾春芳
20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宿白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96岁。宿白是中国考古界的泰斗,更是一位考古学教育家,当今这一领域诸多“主心骨”级人物均出自其门下。樊锦诗正是其中之一,作为授业恩师,宿白先生治学的严谨和严格对她影响极大,而时常遭到的“敲打”和“棒喝”更是让她铭记终生。正是得益于先生如此的言传身教,樊锦诗才一辈子守一不移,终成名家。
四问四答
如今,樊锦诗正带领她的团队做第二卷考古报告。此卷涉及的洞窟结构复杂,塑像和壁画数量多,研究难度大,工作量远远大于出版的第一卷。然而她却说:“再难,我们也要坚持做下去,把报告做出来。”
樊锦诗说:“多卷本《敦煌石窟全集》的考古报告是一个庞大、艰巨、持续的工程。以我现在的身体状况,最多再做两本。多卷本莫高窟的考古报告,是我几辈子都做不完的。但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已出版的第一卷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见批评的声音,算是给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档案,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准确资料。这个报告的准确性,如果我们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那是一定不能公之于众的。这也是宿白先生对我的要求,先生教会我的就是严谨。”她还对我说:“我真的感到很内疚!考古报告拿出来得太晚了,心中一直很不安。”
1981年,宿白先生到敦煌讲学,顺便去看望樊锦诗。到了宿舍,发现桌子上放着一些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材料和文件,就问樊锦诗:“你弄这个干什么?”樊锦诗说,这些是洞窟保护的材料。
宿白先生毫不客气地说:“你懂保护吗?”
樊锦诗说:“不懂。”
宿先生说:“你不懂你怎么管?”
其实,樊锦诗非常明白老师的意思,就是让她好好做学问,做自己的石窟考古,不能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与学术无关的事情上。此时的樊锦诗有苦说不出,因为所里给她的分工是负责主管石窟的保护。
但是,樊锦诗心中非常明白导师对自己的要求,是要她做好石窟考古,让自己不能忘了来敦煌的使命。她暗下决心,绝不能辜负宿白先生对自己的殷切期望,再忙也一定要做石窟考古。
2000年前后,当宿白先生看到樊锦诗送来的莫高窟考古报告的草稿之后,直截了当地问她:“你怎么现在才想起写考古报告了?你是为了树碑立传吧?”这就是宿白先生的风格,他对自己,对学生严格了一辈子,他从来不表扬学生,永远都是“敲打”。他可以对不认识的人非常客气,但一旦发现自己学生有问题,就会直接“收拾他们”。
其实,宿白先生的言下之意是,樊锦诗啊,你终于要回到正题了。因为,当年他把樊锦诗等人送到敦煌时,就对他们寄予厚望。樊锦诗听了老师的话,哭笑不得,内心实有委屈,却也只能说:“宿先生,我拿这个考古报告怎么树碑呢?”
宿白先生这么说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从电视里常看到有媒体采访报道樊锦诗。先生的本意是提醒樊锦诗,不要老在电视里晃来晃去,要专心致志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过了一阵儿,宿白先生又问樊锦诗:“你是不是为了树立政绩?”
樊锦诗笑着回答:“我要是为政绩的话,反反复复地修改考古报告,就不知道把多少当官的机会丢掉了。”
宿白先生不语。
又过了一阵儿,宿白先生三问樊锦诗:“你是不是为了还债?”
还债!这句话撞击着樊锦诗的心,就是还债,确实是还债。这一次她不语,只是点头。樊锦诗暗自心想,是啊!这一辈子到敦煌来干什么来了?不完成考古报告这件事,就白来了。
这个债,在樊锦诗看来,一辈子也还不完,就是把院长当得再好也没用。
宿白先生随即又慢悠悠地问:“你还继续做考古报告吗?”
樊锦诗也慢悠悠地回答:“继续做,问题是考古报告不好做啊。聪明人、能干人都不爱做这件事,那么只有我这样的笨人来做吧。”
宿白先生和樊锦诗师徒之间的“四问四答”,令我突然想到了古代的禅师和弟子之间的交流。法择师,师择人,反过来弟子也要选择师父。选择得当,方能师资道合。宿白先生和樊锦诗的师生关系正是到达了这种师资道合的境界。历史上,只有那些具备真正的智慧、觉悟和见地的人,只有那些无私忘我、持有正念的人,才可能行正确的教授方法。
宿白先生如此这般严谨和严格,时常“敲打”和“棒喝”,现在是很难见到了,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比较脆弱。樊锦诗说,那是他们现在还体会不到什么是上大学,做学问需要什么样的导师。
我想,宿白先生之所以对学术如此看重,缘于北大的人文传统和精神氛围。历史上,北大的大学者全都把学术研究看作是自己精神的依托,生命的核心,把做学问看成是自己的生命所在。
宿白先生的为人和为学,不知不觉也影响到了樊锦诗。有一次,一个年轻的博士上门请教。樊锦诗说:“你既然叫我老师,我就有责任提醒你几个事。不要以为博士就怎么样,你不过刚刚开始,你写的那个博士论文还有问题。听说要给你评优秀,我说你的论文如果评为优秀,就是把你给害了。”
“棒喝”有时可让学生驱散妄念,让学生歇下狂心,正是宿白先生的“棒喝”,教会并成就了樊锦诗一辈子的守一不移。
如师如父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樊锦诗(右)去家中看望宿白先生。资料图片
像宿白先生这样的北大学者,永远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们对人、对社会、对国家的情藏得很深。每次谈到宿白先生,樊锦诗总是充满了敬意和感激,正是这样的老师给予了她一生的影响,如师如父。
樊锦诗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她在北京写论文,而宿白先生恰好外出。但老师挂念学生没有地方住,就告诉樊锦诗去哪儿取他家里的钥匙,可以直接住到他家里去,还说等他回来再邀请她吃饭。
樊锦诗多次拜访宿白先生,他都要留樊锦诗在家里吃饭。可能潜意识中,宿白先生知道,樊锦诗少年离家,常年生活在敦煌大漠,早已把北大和老师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
2016年9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邀访学者项目启动,第一期就邀请樊锦诗回母校讲课。那一次,樊锦诗和老伴彭金章一起回到母校。讲座结束之后,我想请他们二位吃饭,但樊锦诗说他们两人计划去看望宿白先生。据后来樊锦诗告诉我,当时宿白先生已经94岁高龄,见到她和彭金章这两位自己的学生,感到格外开心。他还表扬了彭金章撰写的《敦煌莫高窟北区石窟》考古报告。
樊锦诗说,这样的情况很少在宿白先生身上发生,他从来不表扬学生。不曾想这一次见面竟是永别。一年以后,彭金章先于自己的老师离世,半年后,宿白先生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爱他的学生,离开了他眷恋的燕园,离开了他奉献一生的北京大学。
第二卷莫高窟考古报告快做出来了,可是宿白先生再也看不到了,下一次回到母校,樊锦诗该有多寂寞啊。
樊锦诗和宿白先生高尚的师生情谊让我感到,在这世上总有一类人,在他们独立的灵魂迈向坚定的精神信仰的过程中,总有着常人所无法体会的孤独。然而,这种孤独与他高贵和充实的精神世界同在,并由这高贵而充实的精神,为他深邃的生命注入活力。这样的人,总是站在有益于人类文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潮流之中,也始终处于一种伟大的平和和宁静之中,一切的信念、勇气、力量,真、善、美均从那里流淌而出。
(作者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大学曹雪芹美学与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部高雅艺术进校园特聘专家。著有《意象生成》《戏剧学导论》《她的舞台——中国戏剧女导演创作研究》《戏剧交响——演剧艺术撷萃》等。)
[责任编辑:王露]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