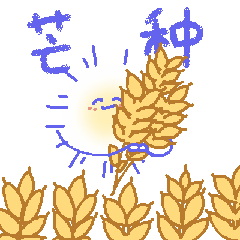芒种丨翻开敦煌“连环画” “粮”辰美景期待住了


独家抢先看
文/陈子怡

6月5日,
芒种节气到了。
芒是指农作物种子壳上的细刺,
小麦、水稻、小米、高粱等
都遍布这样的芒刺。
芒种充满农耕韵味,
夏熟农产要收获,
夏播作物要下地,
春种庄稼要管理,
芒种之“忙”也许超乎你想象……

古诗带你看南北“芒”不同
芒种时节,
南方地区人们忙着插秧种稻。
“水种新插秧,山田正烧畬”,
是岑参描绘的烧荒垦种场景;
“小舟载秧把,往来疾于鸿”,
陆游笔下的插秧是如此热火朝天;
“种密移疏绿毯平,行间清浅縠纹生”,
范成大将整齐的秧苗比作绿毯,
满满的成就感快从字里行间溢出来了。

与此同时,
北方则到了收割冬小麦的关键阶段。
“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
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
在炎炎烈日下抢抓农时辛勤劳作;
“酒沉飧冷未暇尝,腰骨酸辛一骧首”,
酒菜凉了还没有时间品尝,
腰酸背痛只能勉强抬起头来。
白居易、戴栩笔下的刈麦场面,
也许更接近田园生活辛劳的底色。

稻谷丰收之后,
打稻、舂米的任务也相当繁重。
“笑歌声里轻雷动,一夜连枷响到明”,
范成大诗里提到的连枷,
正是打场用的农具,
只需握住连枷把上下甩动拍打,
晒场上的谷物就能脱粒。
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连枷仍是干农活的得力助手呢。

“举臼红颜汗,投舂玉腕扬”,
农妇不停扬腕抬起沉重的石臼,
汗流满面地捶打放入臼中的作物,
两句诗以生动笔触描绘了舂米的辛劳场景。
“鸡窥筛下米,犬舐簸前糠”,
而偏偏在这样忙碌的时刻,
小动物也赶来“添乱”。
舒岳祥寥寥几句,
就将农忙代入感拉满了。

敦煌“连环画”里的“粮”辰美景
镰刀收割、连枷脱粒、石磨磨粉等
大量耗费人力的农事活动,
现今已逐渐被机械化作业取代。
古今田间劳动场面,
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不一样的呢?
千年前的工匠用“连环画”
一帧帧还原了古人耕作日常,
让我们看到充满烟火气的敦煌壁画。

在莫高窟,
专家学者发现了80余幅农作图,
大多采用“异时同图”的绘制手法,
即把各种劳作场景
有序穿插在同一画面中。
从播种、收割到挑运、打场,
“一种七收图”完整呈现了
粮食从农田到粮仓的过程。
在古代敦煌供养人的幻想中,
极乐世界的土地可以“一种七收”:
田间从来不长野草,
一次耕种就能迎来七次丰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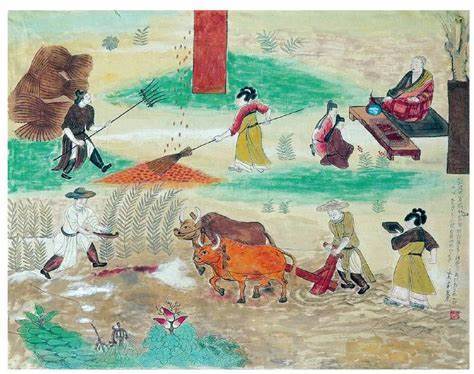
实际上,
岑参所写的“黄沙碛里人种田”,
才是河西走廊农人生活的真实写照。
在深处黄沙瀚海的敦煌
开荒耕作、生生不息,
用千年的瑰丽色彩
将芒种的故事传递至今……
属于莫高窟自己的故事,
也许比佛国传说世界
更有蓬勃不息的力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