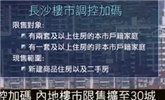回乡路的密码
2019年12月04日 09:11
来源:凤凰网甘肃综合
作者:董国彦
龙泉位于榆中县东南边缘,28个乡镇之一,与定西市的安定区、临洮县接壤。哪里是我师范毕业后扎根十八年的温床,其中一个叫涝坝滩的小地方便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龙泉的时候,回涝坝滩我叫回家。走出了龙泉,我开始叫做故乡。无论如何,总觉得走出故乡的十里山路,有着复杂的密码,多少年都未能读懂。
“精致兰州文墨书香”网络文学大赛优秀奖展播(十五)
回乡路的密码
龙泉位于榆中县东南边缘,28个乡镇之一,与定西市的安定区、临洮县接壤。哪里是我师范毕业后扎根十八年的温床,其中一个叫涝坝滩的小地方便是我出生的地方。在龙泉的时候,回涝坝滩我叫回家。走出了龙泉,我开始叫做故乡。无论如何,总觉得走出故乡的十里山路,有着复杂的密码,多少年都未能读懂。
母亲去世的那年八月,机缘凑巧调进县城的一所学校,但总觉得自己的魂魄还在哪里徘徊,经过的许多事情总是千头万绪地随着鼾声踱入我的梦乡,魂牵梦绕地在山山水水里飘荡,让我沉醉,让我为她彷徨。虽然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照旧回去,就连自己也察觉去的次数逐渐少了许多,不是淡忘了刻骨铭心,也不是淡化了一起摸滚打爬的发小,更不是娶了老婆忘了娘,而是父母不在了,哪里缺少了家的温馨,尽管姊妹们都生活在那方热土,经常念叨我回去,也对我很好,回去之后总觉缺少点什么。他们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也少了扯心的牵挂,也不想去打扰他们,更受不了坐车得一路的颠簸,经不起上班时间请假地折腾……
又是一个周末,去经常坐车的地方,上了开往龙泉的大巴。
车徐徐地开动了,随着车轮的滚动我把目光极力地从透明的玻璃窗户展出去,任思绪在不断地扑入瞳孔的一幢幢楼房和琳琅满目的铺面间自由地滑翔,还没展开昔日的记忆,车开始的摇晃,把我的连重重地碰在茶色玻璃上,玻璃和我的心一样冰凉。路面被切成一方一畦地大大小小坑坑洼洼,前方许多穿红黄马甲工人正在悠闲地修补,我想他们和我一样心里迷茫,是当初路没修好,不堪重压,还是如今的货车司机的头脑被钱熏得发热,超载成了时尚……我不得而知,只好紧紧地攀住前面的凳子的靠背,十里山路的影子在心海里摇晃。
县城以外是312国道,路况比县城好多了,虽有几处起伏似乎要把心提起来抛入空中的感觉,还算一路平展,不知不觉到了高崖。
高崖镇街和涝坝滩的故乡隔着一座山梁。
路在高崖水泥厂门口一分为三,向西的一条穿新营达临洮;西南一条经水坡街道,爬越水泉湾的山梁折向东南,穿过龙泉乡镇府,直达内官营;向东,便能回到我出生的地方。翻一座山,十里黄土山路,并排能过两辆马车,对山村来说可谓宽阔。七拐八缠上了盘路屲,翻山后,八缠七拐绕下大湾山,转过大湾嘴,老家就在大湾嘴的东边山下,两山夹一沟,像站立的“U”。一条难行的蚰蜒路是两山嘴之间的捷径。沟垴叫做阳湾垴。阳湾垴沟是涝坝滩和大湾的分界线。大湾嘴、涝坝滩山、阳湾垴构成平卧的“U”字。从大湾嘴开至阳湾垴,阳湾垴沟浅跨度窄,两边沟坡铲下,沟渠垫起来,便成了坝面一样的路,大转弯,便是涝坝滩地界,再行数十米沟坡筑起缓上坡路,就到了沟沿,接着山路而下,山下便是我出生的地方——洞口,陇海线没开通的时候叫涝坝滩。涝坝滩是歇马店的一个小地名。据说歇马店曾是古丝绸之路上一个节点,解放初是一个农会,后区域有所变迁,但基本维持最初的区域格局。陇海铁路从西向东贯串歇马店,又因曲儿岔隧道当时属于全国长度第二,村名字也与时俱进地变更为洞口。
据说老人说,这条路与共和国同龄,建国初为修陇海线曲儿岔隧道,运送物资方便,特意修开的通道。车水马龙三年之后,1952年陇海线全线正式通车,隧道部队撤走后,便由地方经营。山村人烟稀少,贫穷,马车都是稀物。情况好点的生产队,最多也就有一半辆架子车,架子车对路宽度的要求不严,只要能通过就行。没有人愿意沿着马路多走冤枉。于是这条路部分逐渐被人们冷落,甚至部分路段被蚕食,成了耕地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是一道春风,吹活了一潭死水,也吹醒了老百姓闲置的心情。随着农民日子的红火,越来越多的四轮子、三马子像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在曲折的山路上颠簸蜗行。
在自然力面前,人的力量是渺小的。面对不堪的山路,村里统筹义务工,垫坑筑基,修缮改造,黄土路被重新唤醒。然而黄土高原土质疏松,几场雷雨过后,山里又被打回了原形。就这样,山路在修修补补中绵延着历史的车轮。
“要想富,先修路”,本世纪之初,政府投资,拨巨款改善农村面貌。村里争取“整村推进”项目,修复十里山路中属于村中地盘的部分,成了村道核心建设的内容。被山水冲毁,修起来费工费力,又不属于本村的路段被彻底丢弃,重新规划了新的线路。经过一段时间,山路旧貌换新颜,成了沙路。走上沙沙地响声,那个舒畅很难用语言描述,即使雨天也进出方便,泥水不溅。好处是山里人没啥忙事,雨天很少出门,都呆在家里过天阴。
涝坝滩落后,没有进出的招手停,都是“慢车”惹的祸端。车站附近的人进出都做慢车,招手停也没有跑得意义。所谓慢车,不是跑得慢,而是每站都停。起初兰州-天水,后来兰州到陇西。它有车次,只是频繁更改车次和发车时间,被人们形象地命名罢了。每次回故乡,如果逛过了时间,只有乘班车到高崖,步行翻山来去了。
2000年8月,作为宝兰二线一面飘扬的旗帜的新曲儿岔隧道,完成驻地工作后,为便于运输,十里沙里作为唯一线路重新勘查,因大屲梁上山部分太陡,重新规划。用开隧道挖出的土石,把门前的沟填出一条路,和十里山路外村的部分衔接,形成了现今山路的规模。
十里山路自从建新曲儿岔隧道开始,已不再寂寞,每天四桥翻斗车,从脆弱的山路上呼吸粗重地驶过……
那是我在邻村当老师,后到二十里外的龙泉上班,妻子在甘草水泥厂上班,夫妻两地守望,父母健在,经常两头奔波。除了自己感受到的,就是每逢村里人都发几句牢骚:踏上十里山路,三坑两窖的路面已恢复了曾经。一次从甘草回家,走捷径爬上半山,累了,蹲在较为平坦的路旁休息,一辆运沙车从山顶呼啸而下,满地的沙土随风飞扬,像缀着一条黄龙在半空中腾云驾雾,眼睛半天也睁不开。一辆大车飞过,刚想向前继续前行,另一辆大车满载几十吨重的砂石,从山下蜿蜒而来,发动机轰隆隆地雷吼声震得我的心和脚下的地面在颤抖,车轮碾在路面上,路面好像承受不了似的下陷,裂口。我觉得车轮不是碾在路上,而是从我的心口上重重地揉过去,压弯了我的脊梁,扭断了我的肋骨,心裂了,肺碎了,痛彻心扉,血流满地……
后来,又听故乡人说,工程队施工到半途,缺水了,车拉水成本太高,为解决难题,大动干戈,从高崖压管道直通涝坝滩,其路径大多距离路边不远,于是破植被,掏内脏,根植一条动脉。秋里几场大雨从破碎的地方灌下去,冲涮成了很深的水沟,而且越涮越大。大车碾过去,靠近水沟的地方开始塌方……工程车队熟视无睹见怪不怪,把塌方的地方修修补补得过且过地搞完了工程,拍屁股走了,只留下十里千疮百孔的伤感,无可奈何地在风雨飘摇,几年无人问津。后来有事回去,欣喜地听说来村上挂职的书记——兰州市检察院的领导,为民办实事,已经争取到了资金,准备用水泥把这段面硬化,即将开工,又听说榆中县公路段也拨出资金,用砖铺部分路段。我再没有回去,估计已经修好,百姓不再小心的驾驶,缓慢地爬行……
这次回乡,去参加学生的婚礼不能向东走十里山路,而是向西南走进入龙泉唯一的柏油马路,穿越我工作十八年的地方。好处是随车子的波动,让灵魂飞回一趟故乡。柏油路是我离开龙泉的前一年由原来的沙路铺油的乡镇村道,相信一定畅通无阻,谁知大巴刚使上去,车身开始好似在越野赛车道上跳舞。急忙攀住靠背,把目光伸出窗外,只见原来的平坦的沥青路面已变得坑洞遍布,支离破碎,碎石满地,模样还不如以前的沙路了。车身还是摇晃的厉害,飞石砸在车底盘上砰砰直响。有几个女同志禁受不住颠簸,晕车了。司机也不得放慢速度,左躲右闪避开陷坑,或者挑选两侧相对平坦一点的路面绕行。
和我同坐的是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男子,他说认识我,我看他似曾相识,但具体说不上他姓什名谁。我问他“是谁把刚修一年的路弄成了这个样子”,他不假思索就抖出一串感叹,“都是修兰渝铁路的大车,把路面碾压成了这个样子!铁路修了几年,搁下了,公路成了烂散饭!”
我试探着问他“就没人管吗?”旁座上白发苍苍的老人抢过话头,“谁管得了,不下雨还好点,下点雨全是水洼,车过来泥水四溅——”
他的话戛然而止,车身又开始颠簸摇晃得相当厉害,车上货物互相碰撞、叮当作响。我刚抓牢扶手,行李架上的行李摔下来,砸在前坐上的一个小孩头上,哭声吸引了大家的目光,车厢里塞满了埋怨的声音。
转弯处,司机打了一个汽笛,喇叭的破裂声在风中向远处飘荡。我觉得它的心神也和这路面一样,带着埋怨和无可奈何地波,起伏每一个人的心上……
历史就是在疼痛中向前发展的。现在,宝兰铁路新曲儿岔隧道通车几年,十里山路换了新颜,兰渝铁路全面通车,那段乡道经过几年的辗转,又重新焕发出生机,条条村道四通八达……
静思之,总觉山路上流淌的风携带着记忆的浪漫,也携带着淡淡的忧伤,每一回变迁,都牵动百姓心田异动的密码。
生活是忙碌的。不管你是否走过那段山路,还是走出后忘记了山路变迁的密码,请你挤点时间踏踏山路,唤醒心底蛰伏的乡愁……
作者简介:董国彦,榆中县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发表于《甘肃日报》《金城》《兰州日报》《甘肃诗人》《悦读》《故土》《诗中国》等,有作品入选《中国诗文百家》《中国青年诗选》《金秋之梦·农民文学作品选》等选本。
[责任编辑:陈沛辰]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