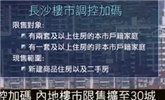三代人一座山 那是他们与祁连的山水依恋
2019年08月12日 23:16
来源:凤凰网甘肃综合
作者:王珊
“天晴了,百灵又飞到空中歌唱起来,千回百转,忽而急促忽而悠扬。一阵雨云过后的雷鸣中,间或还有杜鹃的鸣叫声。山坡上传来狍鹿‘嗷尔嗷尔’呼唤幼鹿的叫声,和熟悉的牧人喊牲畜的声音一样,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天晴了,百灵又飞到空中歌唱起来,千回百转,忽而急促忽而悠扬。一阵雨云过后的雷鸣中,间或还有杜鹃的鸣叫声。山坡上传来狍鹿‘嗷尔嗷尔’呼唤幼鹿的叫声,和熟悉的牧人喊牲畜的声音一样,夏天很快就要过去了。”
14年前,裕固族作家铁穆尔用诗一般的语言,将他在祁连山游牧的经历记录在《蔚蓝色的山脉——祁连山笔记》中。14年后,根据《甘肃省贯彻落实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反馈意见整改方案》,为从根本上减少人为活动对保护区核心区生态环境的破坏,世代在此放牧的牧民开始实施易地搬迁。
目前,核心区149户484人已全部搬出,95.5万亩草原得以休养生息。在离开核心区4个多月后,按照“一户确立一名护林员”的措施,裕固族曾经的山间牧羊人变成了生态管护员,回到了熟悉的大山,继续抒写他们与祁连山的山水依恋。
从祁连山间牧羊人到生态管护员
立秋刚过的清晨,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凉意深深。6:30,东方云破日出,给周围的云层镶上了一层金边,将远处山顶的积雪映出点点光芒。沿着隆畅河一路上行,绕过曲曲折折的山路和无数雨水积聚成的小水坑,两个小时后,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深处的寺大隆自然保护站杨哥资源管护站蓦然出现在眼前。
祁连山山脉东西横贯800多公里,肃南位于祁连山北麓,全县8个乡(镇)102个行政村,涉及自然保护区的就有6个乡(镇)88个行政村。寺大隆自然保护站位于祁连山后山区,是祁连山森林植被最丰富、生物群落最完整、生态功能区划最完整的水源涵养林区之一。保护站工作环境艰苦,不仅海拔高、地理位置偏远,经常断电断网,而且山大沟深、林牧交错、地形复杂。
这里有着一支特殊的队伍,除了站长孙京泉和副站长何长明,其余16人,都是从核心区康乐镇杨哥村搬迁出来的牧民,曾经的他们是和睦的邻居,现在是亲密的队友。
三代人一座山
8:30,队员们收拾好干粮,整顿好马匹,开始了新一天的巡山工作,骑着马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杨哥资源管护站的站长孙京海。翻开他的巡山日志,每一页都写得工整干净,字里行间流淌着对祁连山的细腻感情:“5月14日,星期二,晴转阴……森林植被、柳灌生长正常,无人为活动……在巡山过程中进行了湿地观测,冰雪融化,水聚成坑,河柳已展叶。”
孙京海是一位“老祁连”,从父辈开始,这个家族就一直辗转于祁连山的各个管护站。19岁至今,他已在山中待了40个年头,如今,儿子也继续留在林场工作。对于父母,他感受最多的是遗憾,没有尽到孝心;对于家庭,他说的最多的是感激,妻儿总是全力支持他的工作。
孙京海是整支队伍的核心,也是他将最初像“羊儿一样散布在群山之间”的“新晋”管护员们聚成了一簇坚毅的狼毒花。
每天早晨,孙京海都和队员们一起准时起床,起床的第一件事是打扫卫生,小小的管护站既是工作区也是生活区,每一间房都被打扫得一尘不染,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牧民们之前在山中自由放牧,不受约束,一开始总是找不到人。”孙京海在马背上紧了紧缰绳,“一年来总给他们讲规章制度,讲纪律意识,奖惩结合,现在我们的队伍特别能干,平时若有事不在也会提前打招呼。”孙京海笑着说。
与山为伴四十载,惊险与伤痛一直伴随在这位“老祁连”身边,与狼面对面、在高山上脚踝以下被冰水冻住无法行走以及大雪天滑倒,头磕在坚硬冰面上的经历数不胜数,但他说:“我不能离开山里超过5天,不然心里就会乱得很,一回来,心就静了。”
孙京海是祁连山变化的见证人,80年代的林场伐木,他看到一车车上好的木材被运往山外。禁伐后,采矿“轰隆隆”的声音又开始在山脉之间回响,“河都挖的不是河了。”孙海亮顿了顿,“现在好了,山里安静得能听到风吹过每一片树叶,再也看不到冰冷的采矿机械和过往的大卡车。”他抬起头,嘴里咬着一根白茅草,眼神飘向远方。
云不对雨要来
11:00,巡山队伍沿着羊肠小道向半山腰前行。山高天低,天际线沿着山脉勾勒,在草甸的水洼中倒映出湛蓝的影子,让人误以为草地上开满了紫蓝色的花。走在队伍中间的,是裕固族大姐周艳萍。由于长期在高山上放牧,她的脸颊泛出许多红血丝,走路的时候,漂亮的耳饰一荡一荡,她的裕固族名字叫“萨尔淖尔”,“是月亮湖的意思。”她转过头说,笑容腼腆而清澈。
“现在给我们划的管护地区包括原来自家的草场,巡山时,我们还能走回去看看。”提起搬出的那段时光,周艳萍眼中隐隐有泪光。核心区牧民全部搬出后,对遗留的建筑也已全部拆除清理,这是牧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房子,里面的一砖一瓦都倾注了几代人的感情。最后留下几间作为生态房,作为管护员在深山的休息驻所。
“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忍心再上去,现在好了一些。我们巡山的时间长短不一,远途的话四五天都回不来,到了核心区就住在原来的房子里,晚上看着天上的星星,听着远处各种动物的叫声,仿佛又回到了原来的时光。”周艳萍看着家的方向,声音渐低,“但是搬出来后,原来放牧的草场从稀稀拉拉变成了茂盛浓密,恢复得真好。”
周艳萍的感受反映在了肃南县2018年草原监测调查数据中,针对草原超载过牧问题,肃南县采取舍饲半舍饲养殖、草原流转、周边农区借牧、压缩牲畜规模等措施,全县草原牧草平均高度已经达到19厘米,平均总盖度为78.2%,比2015年分别提高47.8%、18.8%。
孙京海说,现在管护站的职责就是守护好脚下的这片蔚蓝山脉,林区的森林火灾隐患,偷猎野生动物、破坏生态植被,对山水林木做观察记录以及向农牧民群众宣传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都是他们的日常工作。夏季的巡山任务相对较轻,冬天则需每天进行巡查,遇到结冰的水面需要一路撒土才能小心通过,冰面陡峭的地方还需要借助工具双手攀爬,必须十分留心。
到达半山时,队员们席地而坐,一张饼,一袋卤肉,就是一顿午餐,这也是他们巡山的“家常便饭”。午餐过后,队员们将垃圾细心收好,拉回站中集中清运出山。周围积聚的云彩让他们皱了皱眉头,队员罗成站在高处看了看周围,感受着迎面而来的风向,大家一起商量过后断定云中藏雨,此时并未走远,离前方的生态房还有一定距离,安全起见,经验丰富的队员们决定提前结束今天的巡山任务。
我在这里放过牛羊我在这里保护它
下山的路上,队员们唱起了放牧时的歌谣,内心纯朴的他们上一秒还在为养老金的问题发愁,下一秒唱起歌时立马烦恼顿消,嘹亮的歌声回荡在山谷间,让听者的心如山间的云一般,自由辽阔。
37岁的闫文龙是管护站最年轻的成员之一,也是巡山次数最多的成员。从小在祁连山深处长大的他,上马的姿势干净利落,这么多年他一直和牛羊为伴,和山顶的积雪为伴,和雨后的每一道彩虹为伴。
“小时候,小伙伴们会约着一起去放羊,满山跑,羊在远处吃草,我们就躺在草地上唱歌,一首接着一首。我在这里放过牛羊,现在虽然搬出来了,但还能留在这里保护这片大山,觉得很幸运。”闫文龙不好意思地笑,年轻的他爱蹦爱跳,嘴角还有被林木不小心划破的血痕。每一次出去巡山前,站长都会叮嘱,“摩托车能撂,人不能出事,安全第一。”
年岁稍长的罗成是一位藏族大哥,姓氏源于曾经的部落“阿罗家”,“之前我们在里面生活的确会对核心区造成的一定影响,由于平时垃圾很难运出来,一般会烧掉或挖个坑埋掉。”罗成说,“现在塑料袋用的不少,埋下后多年挖开,塑料袋还在那。”
在地势高处,罗成指着掩映在群山中一处若隐若现的平台,回忆道:“夏天的时候,羊儿们会热得不吃草,我们全家就搬到山顶,秋天再下来,那就是我们家扎帐篷的地方。”
牧民们的放牧经验源于祖祖辈辈的口口相传,他们在父母的背上长大,常年追逐着羊群让他们皮肤黝黑,四季轮牧的古老信条刻在他们心中。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约谈,也不懂什么是问责,但是草场过载的变化他们最清楚。当乡镇干部去家中耐心解释为什么要搬出时,虽然心里无比不舍,但他们还是用实际行动全力支持着国家政策,让世代放牧的草场得以休养生息。搬出后,管护站的生活他们也很快适应,并担当起对祁连山新的责任,现阶段,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五险一金”保障能够尽快落实。
据肃南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超载放牧引起的草原生态系统退化曾是祁连山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之一,通过严格实行以草定畜,落实草原奖补资金与禁牧、减畜挂钩政策,采取封栏围育、禁牧休牧等措施,祁连山保护区肃南段有效遏制了草原退化,草原生态正在逐步恢复。
离开管护站的路上,随着车辆逐渐驶出,管护站渐渐缩小成了一个点,队员们的挥手消失在了群山之后,铁穆尔的文字在绵延起伏的山脉中又慢慢清晰起来:“我真真切切地听到,从山下云雾弥漫的森林那边传来唱歌般的声音,这声音包含着迷惘和痛苦,幸福和忧愁,我不知道是风、松涛,还是野兽和大雁之类的飞禽,抑或是这座大山别的什么声音?”(中国环境新闻)
[责任编辑:吴永隆]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