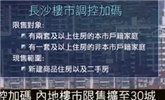敦煌最可贵的守护者常书鸿 来世还要坚守莫高窟
2018年12月10日 12:3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陈俊珺
常书鸿就是这样一个“痴人”,他痴守莫高窟50年,几乎把一生都交付于他所痴迷的敦煌,无怨无悔地守护着这座人类的艺术宝库。
原标题:常书鸿:大爱若痴

常书鸿(油画)克卫作

1991年,常沙娜与父亲在北京合影。

1954年,常书鸿在莫高窟指导工作人员维修栈道。

1991年,常沙娜与父亲在北京合影。
“痴”,在这个时代或许已属罕见,甚至常常和“傻”联系在一起,为人不屑。
其实,无论是搞科学研究,还是从事艺术创作,干事业总需要一些“痴”的精神。这种“痴”,是一种超脱世俗的追求,是一种专注忘我的境界。
常书鸿就是这样一个“痴人”,他痴守莫高窟50年,几乎把一生都交付于他所痴迷的敦煌,无怨无悔地守护着这座人类的艺术宝库。
午后的北京,记者如约走进常沙娜的家,窗前绿植环绕,墙上挂着她与父亲常书鸿的合影,从青春到年迈。
常沙娜从柜子里取出一本画册,那是她年少时跟随父亲在敦煌莫高窟里临摹的画作集。
“你看,这是我跟父亲的学生在159号洞窟临摹的普贤菩萨图,那时候我14岁;这是我17岁时,在290号洞窟临摹的飞天图……”
熟悉的画面一页一页翻过,如今已82岁的常沙娜眼里放射出青春的光芒。她说,看着这些画,耳畔仿佛又响起了莫高窟大佛殿檐角叮叮当当的铃声……
痴迷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敦煌有了最可贵的守护者
解放周末:您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多长时间?
常沙娜:我12岁那年跟着父母去了敦煌,一直到17岁。
解放周末:那段时间,父亲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常沙娜:父亲那时候特别忙,常常顾不上我,但我喜欢跟着大人们进洞窟,看他们工作。后来父亲就抽空给我讲壁画里的故事,教我画画的基本功,让我跟着大人们一起临摹。一个人在洞窟里时,我还会对着墙上的“飞天”唱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长亭外,古道边……”都是当时的流行歌曲。
解放周末:您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艺美术设计家、教育家,还编著了《中国敦煌历代服饰图案》、《中国敦煌历代装饰图案》等,这一切是不是都与年少时在敦煌的经历有关?
常沙娜:是的,父亲给我起名“沙娜”,好像就注定了我们全家与沙漠的不解之缘。
1931年,一个女孩在法国里昂出生,父母借里昂的护城河名“Soane”,为她取名“沙娜”。
常沙娜的童年记忆都在巴黎。每逢周末,家中的小客厅就成了中国留法学生的艺术沙龙,徐悲鸿、王临乙、吕斯百、刘开渠,这些日后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闪耀的名字,她从小就熟知。而在当时,最令这些人羡慕的,是她的父亲常书鸿。
那时,这位只有三十岁出头的浙江青年已留法近十年,是法国著名新古典主义画家劳朗斯最得意的学生。他的画作多次跻身法国国家沙龙展,连续四年斩获三枚金奖和两枚银奖,更有作品被收入法国国家博物馆,前途不可限量。与此同时,常沙娜的母亲也在巴黎学习雕塑。这个艺术之家的生活,如轻快的手风琴般,安定舒适。
一天下午,常书鸿像往常那样溜达到塞纳河畔的旧书摊淘书。一部名为《敦煌石窟图录》的册子吸引了他的目光,里面全都是法国人伯希和在敦煌盗宝时所拍下的图片。常书鸿被迷住了,他第一次知道敦煌在自己的祖国,痴痴地捧着书,直到收摊也舍不得放下。见这个年轻人一连几天都来看这本书,摊主告诉他,吉美博物馆里就有敦煌的艺术品。
从吉美博物馆回来,常书鸿难掩兴奋之情,他激动地对妻子说,自己过去一心倾倒于希腊、罗马的西洋文化,竟不知道自己的祖国还有这么一座不可思议的艺术石窟,真是数典忘祖,不知如何忏悔才好。
“从那天起,敦煌就成了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常沙娜说。
1936年,常书鸿拿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聘书,踏上了回国的列车。
等待他的,并不是梦想中的敦煌。回国后的第二年,抗战爆发,常书鸿刚刚把妻子与常沙娜接回国,一家人就被裹挟进了长达4年的颠沛逃亡,直到他在重庆谋得了一个教育部下辖的职位,一家人才安定下来。不久,长子于嘉陵江边出生,取名嘉陵。
1942年的一天,一场“战争”突然在这个平静的四口之家爆发。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成立,在梁思成、徐悲鸿等人的联合举荐下,常书鸿成为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所长。
“母亲对父亲说,你疯了!要去你自己去,我不去!沙娜也不能去,她还要上学。她对我说,我们好不容易不必再逃难了,现在你爸爸又要到甘肃去,那里连房子都没有。”常沙娜还记得母亲当时的震怒。
不想去敦煌的,何止是他的妻子。在兰州招募工作人员时,“敦煌”二字几乎无人问津。经过苦苦劝说,一名曾在北平艺专就读的学生终于答应跟随常书鸿去敦煌。后来又想方设法招来了文书和会计,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的毡帽,顶着早春刺骨的寒风,开始了敦煌之行。
临行前,梁思成送给常书鸿四个字:“破釜沉舟!”
从此,中国画坛少了一名优秀的画家,但敦煌有了最可贵的守护者。
痴爱 张大千临走时对常书鸿说,“你在这里是无期徒刑啊”
解放周末:在敦煌莫高窟生活的日子,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常沙娜:到那儿吃的第一顿饭我到现在还忘不了:一碗厚面片、一碗醋、一碗颗粒很大的盐。父亲告诉我,这里的水碱性很大,以后每顿饭都要记得喝点醋。父亲在法国的时候习惯喝咖啡,所以把咖啡壶也带去了敦煌,可他喝到的总是又苦又咸的咖啡,因为那里没有糖,而水又是咸的。
解放周末:这样的生活条件和你们过去的日子反差太大了。
常沙娜:我那时候还小,到了那里什么都觉得新鲜。但大人们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最怕的是生病,特别是怕生急病。莫高窟离县城远得很,头一年只能靠一辆木轮老牛车进出,往返至少要一天一夜。我记得研究所有一位职工发高烧,父亲准备用牛车拉他进城,动身前,他含着眼泪说:“所长,我看来不行了,我死了以后,千万别把我扔在沙子里,请你把我埋在土里啊。”病愈后,他就坚决辞职回南方去了。
解放周末:这么苦,父亲有没有后悔的念头?
常沙娜:他刚到敦煌的时候,张大千还在那里临摹壁画,临走时,他对我父亲说“我们先走了,你留在这里可是无期徒刑啊!”但我父亲说,自己是“杭铁头”,就是把“牢底”坐穿,也在所不辞。“杭铁头”是我们杭州人的说法,意思是认定了的事就绝不后悔,永远带着一股子犟劲。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是陈寅恪先生曾经的感叹。
当常书鸿来到心中的圣地,站在曾经轰动世界而彼时已被盗宝者掠夺一空的藏经洞时,他百感交集。突然,“轰”一声巨响,洞窟上方的危檐崩落了一块大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
令常书鸿感到辛酸的是,藏经洞中的珍贵文物早已四散,剩下的千佛洞也一直遭受着自然与人为的双重破坏。在众多无人看管的洞窟里,珍贵壁画早被偷盗者用胶布粘走,剩余有不少被烟熏得漆黑一片,大多数洞窟的侧壁被随意打穿,从鸣沙山吹来的流沙堆积在洞窟里,几十年来无人清理,不少洞窟已被流沙掩埋。
“我父亲是艺术家,但当时摆在他面前的工作却无关艺术,都是实实在在的体力活。”常沙娜说。
当务之急是修建一道围墙,禁止人们随意出入,破坏洞窟。当地人建议,莫高窟的水很咸,只要夯实了,便可用沙土筑墙。于是,常书鸿带领所里人起早贪黑干了50多天,筑起了一道上千米的沙墙。
紧接着是清理沙子。常书鸿估计,洞窟里面的沙子大约已有10万立方米,如要清扫,按照当时的工价,需要300万元,但所里的经费只有5万元。
“父亲和同事们发明了一种‘拉沙排’。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喊着号子,互相比赛,就这样把积沙一排一排刮到水渠边,然后提闸放水,把沙冲走。”
接着,要给数百个洞窟一一编号、普查。常书鸿不得不频频爬到那些早已颓败不堪的残余栈道上,可有些栈道实在无法攀爬,于是,他们又发明了一种叫作“蜈蚣梯”的独木梯。有一次,他和同事爬上九层楼高的洞窟,突然,蜈蚣梯翻倒了,他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只能沿着七八十度的陡崖往上爬,险些摔下山崖。
对洞窟里的壁画进行临摹,更不轻松。临摹洞顶上的壁画时,只能抬头看一眼,低头画几笔,才一会儿,脖子和手臂就十分酸麻。幽暗的洞窟中还需要点蜡烛,烛光摇曳忽明忽暗,眼睛特别酸。
临摹需要大量画笔和颜料,但茫茫大漠到哪去找这些用具?笔秃了,只能简单修理,一用再用;没有颜料,就用红泥、黄泥土法自制。
由于经费短缺,到敦煌不到半年,研究所已债台高筑。为了向敦煌县政府借钱,常书鸿常常只身跋涉戈壁,往返城乡,清晨出发,半夜才归。
许多个梦里,他仍骑着骆驼,在无垠的沙漠中前行,恍惚间,一大块壁画掉落下来,压在他身上。他吓醒过来,只听到大佛殿檐角的铁马铃在夜色中叮当作响。
痴守 “这些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破坏了”
解放周末:父亲有没有对您讲过,他为什么要坚持守在敦煌?
常沙娜:父亲从不对我讲大道理,但我看到的一切都在告诉我,敦煌如果再没人保护,就快毁了。有一次,一个国民党军官来莫高窟游览,向我父亲提出要从洞窟中带走一件北魏彩塑菩萨像,说是放在家中让他妈妈拜佛用。父亲费尽口舌,最后提出用我画的飞天像作交换,才把那个家伙送走。
解放周末:与大自然的侵蚀相比,人为的破坏和掠夺更可怕。
常沙娜:以前张大千在的时候,习惯用透明的纸在墙壁上把壁画印摹下来,然后再画,这样比临摹要快得多。我父亲给我和其他工作人员都立下规矩,决不允许再拓,只能对着临摹。他对我说,沙娜,你把纸钉在墙上,起码要钉两个图钉,那壁画上就会多两个洞,这些东西已经一千多年了,再也经不起哪怕一丝一毫的破坏了。
解放周末:他像爱惜自己的孩子一样爱惜敦煌。
常沙娜:是的,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是他的心头肉。从到敦煌的那年起,他就带头每年种树,他说树木多了,才能为莫高窟遮挡风沙。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惜木如命。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造反派批斗他时,就故意当着他的面砍树。
1945年的春天,妻子突然向常书鸿提出,自己要去兰州看病。一去就没了音讯。
常书鸿心急如焚,策马狂追,跑了200多公里,昏倒在戈壁滩上。抢救持续了三天,当常书鸿醒来时,妻子已在兰州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则与他脱离关系的声明。相守了20年的夫妻,从此成了陌路。
几个月后,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了敦煌,常书鸿则接到了教育部的一纸电文:“抗战结束,百废待兴,国家重建,资金有限,从即日起,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握着电文,常书鸿泪流满面。
“常先生,我们要回家了。”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向他告别。常书鸿无从挽留,他深知经费已经断绝,每个人都思乡心切,熬了这两年,已属不易。
常沙娜说,她至今还记得那个人去楼空的夜晚,空荡荡的莫高窟只剩下她和父亲、弟弟,还有两个工人。万籁无声的夜,常书鸿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他披衣下床,手持一支蜡烛,走进熟悉的254号洞窟。
烛光中,墙壁上的“萨埵那太子舍身饲虎图”他曾经看过无数遍。佛的前身萨埵那是古印度的王子,他看到山崖下即将饿死的老虎母子,就纵身跳下悬崖。此时大地震动,风云变色,他用自己生命的结束换来了老虎生命的延续。此时,张大千的话又在耳畔响起。常书鸿想,如果守在这里真是一场无期徒刑,那他的刑期才刚刚开了个头,绝不能就这么走了。
常书鸿决心放手一搏,去重庆求援。
“1945年的冬天,两头毛驴上分装着简单的行李,我搂着弟弟嘉陵骑着一头,父亲骑着另一头,流着泪离开了敦煌。”常沙娜回忆道:“临行前,父亲把家里能卖的东西全都卖了,作为路上的资费。”
途经兰州时,常书鸿为了造势,举办了一场以莫高窟壁画和景物为题材的父女画展。画展异常成功,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女士很喜欢常沙娜的画。几年后,常沙娜在她的邀请下远赴美国学习艺术。
到重庆后,常书鸿奔走相托,陈寅恪、梁思成、徐悲鸿等一批“敦煌卫士”全力相助,纷纷在报纸上写文章,呼吁挽救敦煌研究所。
常书鸿辗转找到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傅斯年。傅斯年当即决定把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中央研究院的一个分所,解决经费、编制、材料、设备,还拨给他一辆十轮大卡车。
回到敦煌,常书鸿招兵买马,开始了“二次创业”。几年间,郭世清、刘缦云、霍熙亮、段文杰等几十位后来名垂敦煌史册的工作者,纷纷加入了莫高窟保护的队伍。临摹、维修、加固……研究所的工作逐渐恢复并走上了正轨。
痴心 “如果真有来世,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解放周末:父亲在您心中是个怎样的人?
常沙娜:大家都说他是个“痴人”,为了敦煌的事业,他抛却了自我,甚至抛下了自由。在我看来,用一生痴守着自己的信念与理想,也让他拥有了常人体会不到的快乐。
解放周末:对事业的一片痴心,带给他无限的幸福感。而这份“痴”,在今天似乎越来越稀缺了。
常沙娜:是的,但我相信“痴”的力量是可以“传递”的,父亲身上的痴劲,影响了他身边很多人,也包括我自己。他离开后,一代代敦煌人都在追随他的脚步,继承发扬父亲开拓的事业,为世代后人守护这份人类的财富和瑰宝。
如今,在敦煌莫高窟的常书鸿故居里,仍保留着他当年的全部家当:一方土炕、一盏油灯、两张简陋的书桌、几把残破的板凳,还有一架掏进墙壁的土书架……
1954年,这方天地里第一次通上了电。当电灯亮起的那一晚,常书鸿激动得像个孩子一般从这个洞窟跑到那个洞窟,在他眼中,这些上千年的壁画和彩塑好像散发出从未有过的灿烂光辉。他甚至觉得,墙上的侍女都在对他笑。
在常沙娜眼里,父亲就是这么个“痴人”,总能在困顿中寻找到快乐。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里,常书鸿不得不趴在地上给猪喂食。给他平反的那天,他把全所人员喊到家里,其中也包括那些“打倒”他的人。他笑着亲自下厨,做了几大盆法式春卷。
常沙娜告诉记者,她至今保留着父亲曾经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这样写道:“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到了应该把敦煌的东西‘渗透’一下的时候了。”
收到这封信的时候,常沙娜已经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一名教师。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花顶、琉璃瓦的门楣栏板、花岗岩台阶上须弥座的浮雕图案、北大厅墙板的“春夏秋冬”浮雕装饰……在常沙娜参与设计的作品里,几乎都有敦煌元素。
晚年的常书鸿搬到了北京,尽管住在高干楼里,他还时常像个孩子一般喃喃自语:“为什么让我住在这里?我要回敦煌,我还要住我那个土房子!”
常书鸿的家中总挂着一串铃铛,他说,莫高窟大佛殿檐角摇曳的铁马铃声听了50年,现在“客寓京华”,挂上这串思乡的铃铛,聊胜于无。
常书鸿生前始终以“敦煌人”自居,去世之后,按照他的遗愿,仍长眠敦煌。
曾经有人问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常书鸿答:“我不是佛教徒,不相信‘转世’;但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个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去完成敦煌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
[责任编辑:王露]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